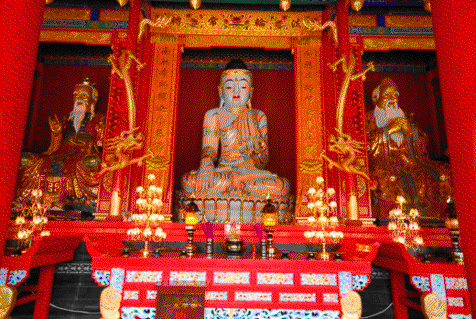|
禅而无禅便是诗——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的哲学解读(五) |
|
六 “故知般若波罗密多, 是大神咒, 是大明咒, 是无上咒, 是无等等咒, 能除一切苦, 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, 即说咒曰: 揭谛揭谛, 波罗揭谛, 波罗僧揭谛, 菩提萨婆诃。”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神妙与澄明, 是无上从而泯灭了一切差别的“真实”, 也是真空实相之理体。这就是《心经》中惟一的肯定, 对“能除一切苦,真实不虚”的“般若波罗密多”的肯定。 那么, 于“空中无色, 无受想行识,无眼耳鼻舌身意, 无色声香味触法。无眼界, 乃至无意识界。无无明, 亦无无明尽。乃至无老死, 亦无老死尽。”乃至“无苦集灭道”, 更至于“无智亦无得, 以无所得故”之语境中, “般若波罗密多”又如何立足呢? 它是不是“道隐于小成, 言隐于荣华。故有儒、墨之是非,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”的“吾生也有涯, 而知也无涯”之中, “彼亦一是非, 此亦一是非。……是亦一无穷, 非亦一无穷也。”的烦恼呢?虽然说“夫实相般若, 即自心之理体;观照般若, 乃自心之妙用。体用不离于一心”, 那么, 它是不是“真如是体, 如如不动”中如“帝网重重”般地“正智是用”之一呢?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。 这一问题, 可以说就是人的“自由”何在的问题。问题的解释, 就在争议甚大、难忘止息的马鸣菩萨所作、真谛所译之《大乘起信论》。《大乘起信论》中说: 摩诃衍者, 总说有二种。云何为二? 一者法, 二者义。……显示正义者, 依一心法有二种门。云何为二?一者心真如门, 二者心生灭门。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。此义云何? 以是二门不相离故。心真如者, 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, 所谓心性不生不灭。 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, 若离心念,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从本己来, 离言说相, 离名字相,离心缘相, 毕竟平等, 无有变异, 不可破坏, 唯是一心, 故名真如。……复次, 分别生灭相者有二种。云何为二? 一者粗, 与心相应故;二者细,与心不相应故。又粗中之粗, 凡夫境界;粗中之细及细中之粗, 菩萨境界;细中之细, 是佛境界。此二种生灭,依于无明熏习而有, 所谓依因依缘。依因者, 不觉义故;依缘者, 妄作境界义故。若因灭则缘灭。因灭故, 不相应心灭;缘灭故, 相应心灭。问曰:若心灭者, 云何相续? 若相续者, 云何说究竟灭? 答曰: 所言灭者, 唯心相灭, 非心体灭。如风依水而有动相。若水灭者, 则风相断绝, 无所依止。以水不灭, 风相相续。唯风灭故, 动相随灭, 非是水灭。无明亦尔, 依心体而动, 若心体灭, 则众生断绝, 无所依止。以体不灭, 心得相续。唯痴灭故, 心相随灭, 非心智灭。 于是, 可以说“性”即所谓“菩提般若之智”, 而“菩提般若之智, 世人本自有之”, “愚人智人, 佛性本无差别”。而这一“性”即“佛性”。凡此种种, 所说出的,不过是一句话——“这个世界并不重要,真正重要的是自我的认定, 即觉” ——“佛”的成就。佛教也如同一切宗教一样,其中的情结不过是对社会的期许和期许中的反思。佛教情结的核心——佛家哲学,以生命为一种“罪责”, 一种人对自己和世界必须负责的“烦恼”而充满对生命的忏悔, 这是中国文化中不能没有的一种“悲剧”精神的补充。中国佛家哲学如果需要一个哲学性的定义, 或需要从哲学意义上来给中国佛家哲学定义的话, 那么就只能说中国佛家哲学在哲学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——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需要“人”去“克己”以“复”之“礼”, 面对这样一种典型的“存在的被遗忘”, 佛家哲学首先说出了“存在”即“无”。 中国文化中从来存在着对“此在”的抗议, 但这一“抗议”却是可怜的, 只能以所谓“清谈”的形式而表现。“清谈”之风, 兴起于东汉末世, 在郭泰、李膺、符融诸人之间似已成风气, 如《后汉书·郭泰传》载: “林宗(郭泰) 通坟籍, 善谈论,美音制, 乃游于洛阳。始见河南尹李膺,膺大奇之, 遂相友善, 于是名震京师。”《后汉书·符融传》载:“融游太学, 师事少府李膺。膺夙性高简, 每见融,辄绝他宾客, 听其言论。融幅巾奋袖, 谈辞如云,膺每捧手叹息。”“清谈”之名, 初见于魏,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劭传》载: “夏侯惠荐劭曰:‘臣数听其清谈, 览其笃论, 渐渍历年, 服膺弥久。’”至于正始之间, 蔚然为一时风尚所在。《晋书·王衍传》载: “魏正始中, 何晏、王弼等, 祖述老、庄立论,以为天地万物, 皆以无为本。无也者, 开物成务, 无往不存者也。阴阳恃以化生,万物恃以成形, 贤者恃以成德, 不肖者恃以免身。”但如《晋书·儒林传》所说“清谈”之罪至于“五胡乘间而竞逐, 二京继踵以沦胥。运极道消, 可为长叹息者矣。”则未免过苛。如“刘伶纵酒放达, 或脱衣裸形屋中”, 如“诸阮皆能饮酒, 仲容至宗人间共集, 不复用常杯斟酌, 以大瓮盛酒,围坐相向大酌。时有群猪来饮, 直接去上,便共饮之”等等, 虽然不能否认是价值失落、“存在”中的“光明”和“想象”消失后, 以“荒诞”形式表现出来的对“存在荒诞”的一种抗议;但这一“抗议”之所以无力, 又不仅在实践上, 更在其理论上,诚如钱穆先生所言“若阮遥集之蜡屐自若,庶乎可以忘人;王子猷之到门即返, 庶乎可以忘我。忘人是无环境也, 忘我是无趋向也, 若是而见其自我之真焉。此晋人之意也。故其礼法有所不顾, 世务有所不问,而一切惟自我之无累为贵;而世以礼法世务责之, 宜其不相入也。然晋人之所谓‘我’者, 终亦未能见‘我’之真也。何则? 晋人以‘无’为本, 趋向不立, 则人生空虚, 漂泊乘化, 则归宿无所。知摆脱缠缚, 而不能建树理想。知鄙薄营求, 而不免自陷苟生。故晋人之清谈, 譬诸如湖光池影, 清而不深, 不能具江海之观, 鱼龙之奇;其内心之生活, 终亦浅弱微露,未足以进窥夫深厚之藏, 博大之蕴也。”
|